
单位下属的一个小单位的院子里,一片空地上长满了各种果树。数目最多的要数柿树了。这个院子频临街道的旁边,来往行走的人,柿子树都能给他们一年四季的惊喜:春天,枝头上绽开的嫩绿的芽儿,长得慢,似乎好长时间都是满眼翠绿;不经意间,绿叶间冒出了小礼帽似的黄色的花朵,也是很慢,十天半月之后,一个个小柿子才从花瓣中露出青涩的脸庞。然后,花瓣脱落,柿子也还是在慢慢腾腾地在膨胀着、椭圆着......
夏天是水果生长的季节。即便如此,渐渐长大的柿子,不恣肆,不张扬,把圆圆的脸庞隐藏在已经宽大厚实的叶子间,不仔细看,你基本上看到的是满树绿叶,总以为这棵树没结果。但到了冬天,随着秋风吹拂,寒霜降临,柿树的叶子一片片飘落下来,金黄金黄的颜色,铺在地上,犹如一块金色的地毯。叶落果现,光秃秃的枝头上挂满了盏盏“灯笼”,它们和枝干——母亲依然不离不弃,一眼望去,满目殷红,好不壮观!
不知是不好攀爬树干,还是碍着寡欲和自尊的意识,满树的黄柿子就这样一直地挂在树上,之后,慢慢地变红,甚至掉落在地上。不过,也还是有没有的时候,几乎一夜之间,满院子柿树枝头上的灯笼便没有了踪迹,也许这个单位在哪一天派人摘下来,在寒冷的冬季作为福利分给了员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资源共享。
每每看到这满院满树的红灯笼,我的思绪便会油然地飞到了已经久远的童年时代。生养我的村庄,是个山村,村子以西的山坳里,沟沟坎坎,乃至平地上长了数百棵柿子树。有一处规模最大,足有十几亩地,成排成行地生长着不同年龄的柿子树,兴许是韩氏人家的柿子园吧,村里人都叫它“韩柿园”。集体经济之后,都由生产队出人出工分料理柿园,果实按人头分给大家。后来,土地分到户,柿子树也分到了户。我家也分到了两棵。树大根深,平时基本上不要问事,就等着秋后收获果实就行了。那几年,柿子大丰收,一到柿子收获季节,村子里的人都大篮子小笆斗地挎到集市上出售。我也跟大人们去过几次,因为山区的柿子个子大,鲜灵,一到市面上便被销售一空。那时的零花钱,除了卖鸡蛋,也就是卖柿子和卖山芋了。
当时被农村人羡慕的城里人,素质也不一般齐。大部分人规规矩矩地按价付款,但也有极少数人乱中取巧,趁众多人买柿子的时候,捡大个的拿了几个就走,卖柿子的人因为太忙也不易发现。可是,等到卖完了之后,一算,斤两和收到的钱数不符,才知道可能是有人从中占了小便宜了。也罢,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吃亏人常在,财去人安泰。
如今,我的家乡皇藏峪(刘邦曾经藏匿的一片森林)由于开发国家级森林公园旅游项目,原先那些个生长柿子树的土地上,早已被修了宽阔的柏油路,或种上了花枝招展的樱桃树、桃树、杏树、木瓜树,以春天的绿红和秋天的累果,招揽游客。但是,柿子树还是有的,不过它们已经不是生长在原先的阔地上,沟沟坎坎上,而是现身于村子里房前屋后的空地上了。这些后来在房前屋后栽种的柿子树,也像我们单位院子里的柿子树一样,四季葳蕤红火,煞是喜人。每年初冬回老家给祖坟烧纸,回来时,左邻右舍,婶子大娘,除了给我们带些山芋、南瓜以外,总会从自家的树上摘下一嘟噜一嘟噜的经霜柿子和金黄色,闻起来有股醇香的木瓜。这让我一直没有忘却的乡情徒生了几分厚重。

汪曉佳先生
作者简介:
汪曉佳,1952年出生於安徽蕭縣,1969年入伍,從軍六年。退伍後在皖北一座煤礦工作,後調入礦務局機關,先後從事辦公室和宣傳工作,歷任局辦文書科副科長.科長;局宣傳部外宣科科長,文聯秘書長,副部長。
曾出版個人文集《鑽草屋》,《住高樓》,《驀回首》,為中國煤礦作協和安徽省作協會員,淮北市作協副主席。現已退休賦閒,生活之餘仍堅持寫作,其散文作品時有見諸報端。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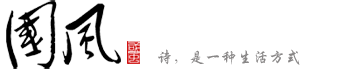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