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朝之音
由于元词离宋未远,所以元词基本上是相沿两宋尤其是北宋词人的路子走下去的。这是因为历史又一次重复或者说是进步了,当元统一中国,两国交战的厮杀声渐去渐远,人们又恢复到相对稳定的生活之中,而相对稳定的生活恰又是婉约生长最好的环境。因此,在元代无论是大词人白朴还是张翥,也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他们词作风格基本上是和顺婉转,都带着两宋印记,都能找到、看到、听到前朝词人创作的痕迹。
一、赏析张弘范的词
张弘范是河北定兴人,任蒙古汉军都元帅。在攻破襄阳后,率左翼兵团循江汉南路直捣临安。攻陷临安后,又率元朝水路大军一直追击南宋军队于崖山海面,终于消灭了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并捕获文天祥于五岑坡。他威逼文天祥,让文写信劝降在海上坚持抵抗的南宋张世杰部。同时追杀八岁的南宋最后的皇帝,陆秀夫被逼背负帝昺跳海而死,随同帝昺的南宋臣民皆随皇帝一同投海殉国。三日后,崖山海面浮尸十万余具,其情景惨烈之极,令后世之人无不泪满衣襟,这皆为张弘范所为。而张竟在崖山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于石上。身为汉人,灭汉于斯,竟勒石记功,比一比为国尽节的文天祥和十几万投海而亡的南宋大汉子民,你张弘范算是个什么东西。
就算张弘范不是个东西,可他的婉约词却写得十分清丽,大有北宋晏几道之风。请读他的《临江仙》:
千古武陵溪上路,桃源流水潺潺。可怜仙侣剩浓欢。黄鹂惊梦破,青鸟唤春还。 回首旧游浑不见,苍烟一片荒山。玉人何处倚阑干。紫箫明月底,翠袖暮云寒。
一个大军统帅在征战中,途经武陵,面对眼前的美景想起了自己相悦的女子,写下了这首幽怨缠绵的情词。其情意是真挚的,其情调是凄迷的,该词的风格与小晏极为相近,也是张弘范的代表作。如小晏《鹧鸪天》之“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以及《蝶恋花》之“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在写离别之感时,含蓄蕴藉,情意深长。历代词论家对这首作品皆十分看好,沈雄在《读古今词话》云:“《淮阳乐府》(是张弘范词集名,笔者注)不作夸大语。其《临江仙》有曰:紫箫明月底,翠袖暮云寒。风调不减晏小山,可知元之武臣,亦有能词者。”细读这首词的确是情深意真,委婉曲折,清丽含蓄,颇有意境。所以清陈廷焯在《词则·别调集》中亦云:“从古大英雄必非无情者,吾于仲畴(张弘范字仲畴,笔者注)益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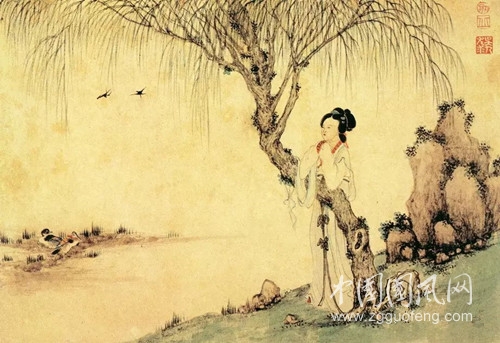
正如小晏在他的词序中所言:“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夜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镜缘之无实也。”而张弘范在他的另一首小令《点绛唇》中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心情,词曰:
独上高楼,恨随春草连天去。乱山无数,隔断巫阳路。 信断梅花,惆怅人何处,愁无语。野鸦烟树,一点斜阳暮。
这首词和前首《临江仙》相同,都是忆旧、怀人之作,只不过这首词更含蓄,更婉转一些。上片三句一出,马上使人进入李白《菩萨蛮》词中“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的意境;又使人想起晏殊《蝶恋花》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那种临秋望远的景致;更有秦观《八六子》和李煜《清平乐》词中所表述的楼头远眺,离恨恰如春草的那种感慨,所以意蕴极为丰厚,耐人咀嚼。下片则更是渐入佳境,且直奔主题,他化用南朝陆凯江南寄梅的典故,相问伊人在何方。尤其结句“野鸦烟树,一点斜阳暮”,以景结情,风致妍然,不仅化用秦观《满庭芳》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的词意,还兼有范仲淹《苏幕遮》“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的境界,同时还有辛弃疾《摸鱼儿》中“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感慨。虽然该词化用众多前人词意,但词人信手拈来,贴于己词,竟不着痕迹,且又能准确表达出缠绵悱恻的怀人之情,不能不说张弘范的艺术功力是十分高超的。
在张弘范的《淮阳乐府》集中,还有许多优美的小令和极精美的联句,都是表现怀人念旧思绪的。如在《点绛唇·咏海棠》中“十年南北,几度空相忆,把酒留名,后会知何夕,愁如织”。在《点绛唇·赋梅》中则又有“昨夜幽欢,梦里谁呼去,愁如许”。这就更神似小晏词风了。词人在《清平乐》中则又唱道“关河南北,有雁无消息,落日楼头人正忆,啼鸟一声山碧”。它的佳妙在于,以抒情为主,情寓景中,把思妇的九曲回肠和青山骋望而有机结合,写得极切极婉、极柔极厚,确有北宋小令之风韵。也许是元朝与宋代相近,元词去宋未远,在张弘范的小令中积淀了两宋时期许多婉约词人的词意。如张词《青玉案》中“一川秋意,满怀愁绪,楼外潇潇雨”句,正是使用贺铸《青玉案》中的句法“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黄子梅时雨”。只不过就形式而言,张词用在上片,而贺词则在下片;就内容而言,贺铸是路遇佳人而不知所往而产生的愁绪,而张词的本义则在下句有了注解即:底事相思肠断处,则说明了张是相思之苦。贺铸叠写三句是言愁,而张词叠写三句则是言情。这真是既同曲又同工,巧妙之极矣。
二、赏析梁曾的词
在元代前朝的婉约派词人中,梁曾是不可或忘的一个词人。在全金元词中,梁曾仅存词一首,而这一首却因格调俊雅,为后世词论家所推崇。现赏析他的《木兰花慢·西湖送春》:
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算春色三分,半随流水,半入尘埃。人生能几欢笑?但相逢、尊酒莫相催。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绕珠围。 彩云回首暗高台,烟树渺吟怀。拼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西楼半帘斜日,怪衔春、燕子却飞来。一枕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
古往今来,凡写送春者,无不为悲怀哀怨。而该词却清奇洒脱,充满赏春的逸兴奇思,一改千古以来此题材的伤婉之语,从而又开送春的独特新境,这也正是该词的精妙所在,恰也是后代词论家极为看好该词的原因。明杨慎在《词品》中评论该词时说:“此西湖送春词,格调俊雅,不让宋人手。”而清徐釚在《词苑丛谈》中则又说:“观此词,孰云元人诗余不如宋哉。”徐釚的评价则比杨慎的评价又递近了一层。该词开篇设问就极为精警,词人首先化用晚唐温庭筠《惜春词》中“百舌问花花不语”的诗句,又化用宋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词意。由于化句妥帖自然,已使开篇不凡又意蕴丰美。接下去的“算春色三分,半随流水,半入尘埃”三句,又化用苏东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词意。最妙还是上片结句的二句“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绕珠围”,又化用刘伶《酒德颂》诗中的成句“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仅化用的浑然天成,而又以“千古”对“一春”的精妙绝对,使这首词的品位陡然上升,已成元词中最精美之作。然而,此刻词人心意未完,笔力尚健,在下片又以“拼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句,不但使该词在元词中有翘首之位,而且可与历代写送春的佳作相媲美。清词论家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对梁词此三句的风韵极为赞赏,将他与黄庭坚、王观、王沂孙的咏春相比,在对比之中,梁词的艺术魅力呼之欲出。他说:山谷云:“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通叟云:“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碧山云:“怕此际春归,也过吴中路。君行到处,便快折河边千条翠柳,为我系春住。”三词同一意,山谷失之笨,通叟失之俗,碧山差胜。终不若元梁贡父云:“拼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为洒脱有致。上文所言山谷即北宋黄庭坚,引句为所作《清平乐·春归何处》词;王观字通叟,引句为所作《卜算子·送鲍洁然之浙东》词;南宋王沂孙字碧山,引句为所作《摸鱼儿·洗芳林夜来风雨》词。只不过查由唐圭璋主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宋词》与吴衡照所引王沂孙的词在标点上有所差异(详见《全宋词》第五卷第3362页)。应当说此四人对春之留恋之情,梁曾词确实更情直俊利些,而且在俊利中又含潇洒,别有一番风情。尤其是结句之“一枕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句,留下了使人怅然若失的余韵,这的确是一首传之千古的名作。
三、赏析张玉娘的词
她是元代少有的女词人之一,字若琼,号一贞居士,著有《兰雪集》传世。据史料载,她是前宋提举官张懋之女,有殊色、知书,敏慧绝伦。少许字沈佺。因沈佺有疾,既而父母欲违约,玉娘不从。亲自寄书给病中沈佺,以明心志,并以死自誓,非沈不嫁。但适沈不久,沈即病亡,玉娘郁郁而终。由于婚姻的不幸,张玉娘写出许多优美的词篇。她的词于柔思绮怨中,时挟东坡之清气,可继轨李清照、朱淑真。

请读她的少女之作《玉楼春·春暮》:
凭楼试看春何处。帘卷空青澹烟雨。竹将翠影画屏纱,风约乱红依绣户。 小莺弄柳翻金缕。紫燕定巢衔舞絮。欲凭新句破新愁,笑问落花花不语。
从词中不难看出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在暮春之时,听雏莺鸣啭,看紫燕垒巢,其乐何如。只是看到风吹红乱,心中才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新愁,而这种新愁正恰如辛弃疾《丑奴儿》上阙中少年人的心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张词中“凭楼试看春何处”,说明她只是若有若无地问一句,春天呀,你要哪里去?远不如黄庭坚《清平乐》中“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归处,唤取归来同住”那样辞情恳切。尤其是结句“笑问落花花不语”,更是体现出少女的憨态可掬,更不似欧阳修《蝶恋花》中“泪眼问花花不语”的心境。词人把一个美丽少女的心态和形态都以极其轻柔清丽的语言描绘得活灵活现而又亲切感人。这种美好的少女生活在张玉娘《苏幕遮·春晓》中亦曾再现。但是生活毕竟是严峻而又冷酷的,当张玉娘嫁到沈家未几,年轻而貌美的郎君(张玉娘呼之为玉郎,可见其貌美)就因病而亡,这使得倘在幸福中的词人一下子坠入痛苦的深渊,她的词作也一改往日的清丽和婉而变得凄清哀苦。丈夫一去不回,而且是永远地回不来了,在《玉蝴蝶·离情》中词人唱道:“玉郎应未整归鞍。数新鸿、欲传佳信,阁兔毫、难写悲酸。到黄昏。败荷疏雨,几度销魂。”她是十分钟爱丈夫的,更是十分想念已经走远的亲人,在《水调歌头·次东坡韵》中,词人伤心地唱道:“玉关愁,金屋怨,不成眠。粉郎一去,几见明月缺还圆。”她已经又感到现实的冷酷。在《卖花声·冬景》中,她写道:“冷浸宝奁脂粉懒,无限凄清。”而且,词人也一天天地消瘦起来。在《如梦令·戏和易安》中,词人已是“何事黄花俱瘦”。可是词人又能去问谁呢?她也只能“不禁清冷,向谁言著”《忆秦娥·咏雪》。于是乎,词人“尽日花枝独自看”,而且是“愁绕春丛泪未干”《南乡子·清昼》,对逝去的夫君强烈的思念,终于使词人病倒了,卧病在床仍遏不住相思,词人在《玉女摇仙佩·秋情》中写首:“细思算、从前旧事,总为无情,顿相辜负。正多病多愁,又听山城,戍笳悲诉。”词人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也许是生活改变了她,病中的词人现已是“任钗横鬓乱,慵自起来偷整”《法曲献仙音·夏夜》。在这时,我们不但看到一个“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还看到一个“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的李清照;一个“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李清照和一个“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夜间出去”的李清照,李清照几个时期的形象一齐走到我们面前,她就是此时的张玉娘。难怪许多词论家在论及张玉娘词作时,一再阐说其有李清照之风韵。当代词学家们在《读元词札记》中,也评价张玉娘小令极为凄凉,词风清新婉丽,明显受李清照之影响。
虽然张玉娘词的内容比李清照的内容狭窄的多,而其艺术功力也远逊李清照,而就整个元代而言,也只有张玉娘能勉强地接下由李清照传来的接力棒了。

【作者简介】耿汉东,安徽省淮北市人,诗人,文学评论家,地方文化学者。先后供职于中共淮北市委宣部和淮北日报社。喜欢读书,敬畏文字,己创作出版17部作品,主编8部诗集。现为安徽省诗词协会副会长、淮北市诗词学会主席。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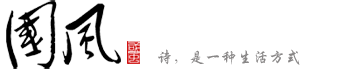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