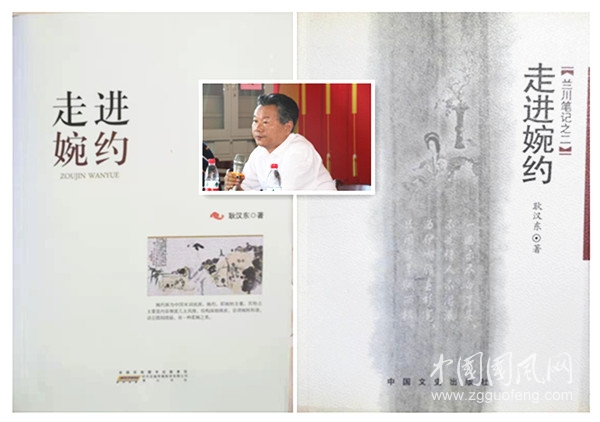
婉约之愁
婉约派的词人们大都是多愁善感的,言愁便成了他们写作的主题。由于婉约的词人情感丰富,因此对愁的描述也随之丰富起来。愁是人们的一种感情思维活动,是极为抽象的。本文不想涉及他们因何而愁,只想写出他们是如何而愁,以及他们是如何极形象化地表现愁,从而使人们更真切、更准确地了解词人心中之愁,并以此来阐释婉约的主题。那么,古人们是如何言愁的呢?
一、形式多样
(一)、春愁。时序的变化能给词人们带来愁绪,尤其是春天。春天里百花盛开,万紫千红,正是人间最美好的时节,可是在词人的笔下写出了春愁。南唐冯延巳在《蝶恋花》中首先唱出“撩乱春愁如柳丝”;而北宋柳永则在《凤栖梧》中继则唱出“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南宋的蒋捷在《一剪梅》中又唱出“一片春愁待酒浇”。
(二)、新愁。不仅如此,愁还有新旧之分,冯延巳在《鹊踏枝》中无可奈何地唱道“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而柳永则在《竹马子》中发出“新愁易积,故人难聚”的感叹。年轻时的李清照则在与丈夫赵明诚分别后,在《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情不自禁地吟道:“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贺方回则在《石洲引》中写出“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新愁”的惆怅。
(三)、清愁。正像新愁、春愁一样,在词中使用清愁的有许多。现略举几例:
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
———宋·辛弃疾《粉蝶儿》
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
———宋·辛弃疾《汉宫春》
关河无限清愁。
———宋·岳珂《祝英台近》
愁与西风应有约,年年同赴清愁。
———宋·史达祖《临江仙》
仗酒祓清愁。
———宋·姜夔《翠楼吟》
动庾信、清愁似织。
———宋·姜白石《霓裳中序第一》
(四)、闲愁。闲愁在词中使用的频率很高。
风流后,有闲愁。
———宋·柳永《庆佳节》
见闲愁,侵寻天尽头。
———宋·贺铸《更漏子》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宋·李清照《一剪梅》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
———宋·辛弃疾《摸鱼儿》
赢得闲愁千斛。
———宋·辛弃疾《念奴娇》
(五)、离愁。在所有的“愁”中,离愁最苦,也写得最多。王沂孙在《高阳台》中就唱道“江南自是离愁苦”。那么,离愁能苦到什么程度呢?不可说也。柳永在《倾杯》中只说过有“离愁万绪”。有一万种离愁的情绪那的确无可言状。能否再具体些,再形象些呢?李后主在《乌夜啼》中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我们能知其形状却不知其数量,仍不如柳永和姜夔说得较清晰些:张先在《一丛花令》中说“离愁正引千丝乱”;姜夔则在《长亭怨慢》中说“难剪离愁千丝”。这样,我们对愁又有了数量的概念,它似丝状的东西,或柳丝、或蚕丝、或绸丝。既可以用剪子剪断,还可以手予以理顺。总之,它虽然细小,我们能看到并能触摸到了。可见词人们已把离愁物化了,但能否将其更具体些呢,不然南宋咏物名家王沂孙在《齐天乐》中何必提出“重把离愁深诉”的质疑呢。但他也仅是质疑而未描述出更形象化的离愁,还是他的前辈词人辛弃疾做得好,在《满江红》词中,词人要“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可见离愁是瓦罐、酒杯一类的东西了。然而把离愁敲碎又当如何呢?北宋词人贺铸在《宛溪柳》中说“回首离愁满芳草”,原来敲碎后的离愁竟是一片青绿。这一来,我们终于把离愁看清楚了。

二、状态各异
古人们对愁的描述多用比拟的手法来抒发感情,表现词人忧时伤世的心态,极为耐人寻味。词人们首先使用拟人法,即用人体的某一部位来言愁。有的以眉言愁,如韦庄在《荷叶杯》中说“一双愁黛远山眉”,接着晏殊在《玉楼春》中唱出“窗间斜月两眉愁”,而小晏则在《蝶恋花》中吟唱“弯环正是愁眉样”。有的以目言愁,张元干在《贺新郎》中写出“倚高空愁目,气吞骄虏”。还有的是以心言愁,如汪元量在《莺啼序》中低吟道“未把酒,愁心先醉”。使用“愁肠”的比较多,南唐李煜在《清平乐》中含泪吟道“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北宋范仲淹虽然坐镇西北,拥兵自雄,但每当羌管声声的霜夜之时,仍有“将军白发征夫泪”之慨,故他在《御街行》中有“愁肠已断无由醉”的低吟,在《苏幕遮》中更有“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伤情。另外还有一些词人虽未明确的使用,但也与人有关,如:柳永在《戚氏中》有“追往事,空惨愁颜”;陆游则在《钗头凤》中用“一怀愁绪,几年离索”来哀叹逝去的爱情;吴文英在《踏莎行》中用“艾枝应压愁鬟乱”来表达他感梦怀人的心情;更有甚者,北宋的晏殊在《踏莎行》中竟有“一场愁梦酒醒时”之叹。
其次使用拟物法,用自然景物来述愁。冯正中在《鹊踏枝》率先唱出“缭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晏几道则在《鹧鸪天》里有“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拼得为花愁”。还有写云愁和烟愁的,王禹偁在《点绛唇》中就说过“雨恨云愁”;吴文英则在《点绛唇》中说过“卷天愁云”;而晏几道则在《踏莎行》中有“细草愁烟,幽花怯露”。这是用自然界中比较小的事物来言愁,人们是便易接受的。可是词人们还有更新鲜的而且用较大事物来述愁,虽然没有上述例句形象,但仔细读来,也还是很有趣味的,现举几例:
不会长年来,处处愁风月。
———宋·贺铸《愁风月》
城中桃李愁风雨。
———宋·辛弃疾《鹧鸪天》
满城似愁风雨。
———宋·刘辰翁《永遇乐》
怅望故园愁。
———宋·张元干《水调歌头》
能携带的愁。词人言愁不仅描绘出它的形式和状态,还赋予它生命,并测出它的重量,轻则可随身携带,重则可车装船载,真可谓活灵活现。贺铸在《小梅花》中说“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可见愁是自行来的,无人相邀。而柳永在《燕归梁》中则说“愁只恐下关山”,这是说愁在离去时还有点顾忌。词人们能写出愁的喜怒哀乐,可见它是一个生灵了。尤其是秦观在《满庭芳》中写道“谩道愁须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这不是有生命的吗?不然,它何以自行来去。
但是,词人们还是更多地将愁随身携带,不让它自行行走。例如:
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
———宋·周邦彦《夜飞鹊》
故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
———宋·吕本中《减字木兰花》
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宋·辛弃疾《祝英台近》
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
———宋·张炎《绮罗香》
在《绮罗香》里,张炎将愁不是随身携带,而是用载,可见愁则十分沉重了。至于言愁之重,古代诗人们描述得较明白,譬如大诗人杜甫则是以山喻愁(或忧),他说“忧端如山来,澒洞不可掇”。而赵嘏则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半多”。那么这也太重了,山何其大,何其重,若带走非人力可为也。可词家们言愁则未有其重。正如张炎所云“载愁”,既然是载,那也只可指车船之类了。李清照在《武陵春》中说道“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形如蚱蜢的小舟充其量也只不过能载三千斤吧。随后辛弃疾也在《水调歌头》唱道“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古人们是把恨、悲、忧都归言愁一类的。我们若把离恨与离愁等同论来。还有几个词人以舟载愁的如:
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宋·陈与义《虞美人》
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宋·苏轼《虞美人》
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宋·郑文宝《柳枝词》
载取暮愁归去。
———宋·张元干《谒金门》

三、如水之愁
以水喻愁者,查阅古曲诗词时会发现许多经典之作。唐代诗人李颀所作边塞诗,风格豪放为时人所重。但他所作一首五绝却成为后代婉约派作家以水喻愁的始祖。其诗曰:“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诗中主人之愁竟似那浩渺的东海之水,愁何其深矣。后代词人只有秦观尚可匹敌,他在《千秋岁》中以凄厉之音唱道“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正如他的同代人曾布所云:“愁深如海,岂能存乎”。这的确是秦观最后的哀音,在此之前,秦观曾在《江城子》中还唱过“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词人江水自喻胸中之愁这是非常恰当的,当然,秦观是化用李煜的词句。真正把如水之愁写到极致的是被后人称之为“词中之帝”的李煜《虞美人》,其词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已为千古经典。自然,李词也是脱胎于白居易“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的诗。同样以江水喻愁的,南宋范成大在《南乡子》中“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向西流”句,则笔力弱矣。远不如刘禹锡在《竹枝词》所唱“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那样流畅,那样自然,那样贴切。说到流畅和自然,北宋欧阳修在《踏莎行》中所写“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则更是令人赞赏不已。同时李清照在《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有“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也显得优美自然,词人已把心中之愁和楼前流水溶为了一处。当然李词喻愁远比前文诸家气魄小多了。但还有更小的如:范成大在《眼儿媚》中曾唱道“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范是将内心的愁比作细小的波浪。无独有偶,南宋姜夔在《小重山令》中也曾把心中愁绪比为“斜横花树小浸愁漪”,而涟漪则是河中最细微的波浪了。
四、愁归何处
南唐冯正中曾在《鹊踏枝》中言道“满眼新愁无问处”,这说明词人即满腹忧愁愁满世界,他的隔代弟子北宋宰相晏殊与欧阳修与乃师就有同感,晏殊在《踏莎行》说“无穷无尽是离愁”。而欧阳永叔则在《踏莎行》中说“离愁渐远渐无穷”,这都说明词人心中愁多。让人们不明白的是,三人同列宰相,位极人臣愁从何来?可冯正中仍不依不饶,在《采桑子》中仍在说“起来点检经曲地,处处新愁”。当大官的享受着荣华富贵的这样说,而数度被贬出京师的小官吏们也这样说,晁补之在《水龙吟》说“人愁春老,愁只是人间有”。看来是人间处处有忧愁,那么,愁从何来?
柳永在《凤栖梧》中说“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春愁仿佛从天边走来。而清代词人蒋春霖则在《卜算子》中说“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这愁又向天边走去。柳蒋二人终生穷困潦倒,将身世飘零之感寓于其中,读其词令人倍感凄婉那是可以理解的。可南宋张玉田在《八声甘州》中亦有“无避秋声处,愁满天涯”句,这愁也太大了些,当年的贵介公子怎有如此的感叹呢?实际上,愁在哪里?愁在词人的心中。正如南宋吴文英在《唐多令》中所言“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真是一言蔽之。故尔,韩缜在《凤箫吟》中“锁离愁,连绵天际”,以及张玉田在《台城路》中“荒台只今在否,登临休望远,都是愁处,”就十分好解了,因为词人心中有愁,愁从心中来,所以才愁满世界。
那么,愁归何处?
先从小处说起:南宋史达祖在《绮罗香》中说“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在春雨潇潇后的岸边,愁就在那里,只不过被晚急的春潮带走了而已。还有更小的更具体的去处,张炎在《高阳台》上说“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词人笔下愁就在西湖边上白鸥的面前。稍微大一些的愁处应数南宋姜夔在《念奴娇》中的“愁入西风南浦”,在一条河边上,有愁在焉也。而清代王士祯则在《浣溪沙》中说“断鸿无数水迢迢,新愁分付广陵潮”,词人把心中无限愁绪尽付于广陵潮水了。上述例句,对愁的去处都交代地非常清楚,愁大都处于临水处。而清代词人况周颐却不愿将愁尽放在水边,他在《苏武慢》中说“愁入云遥,寒禁霜重,红烛泪深人倦”,词人要把愁放在长空中。其实,愁在水里也罢,空中也罢,都没有南宋刘辰翁在《柳梢青》中说得好“铁马蒙毡,银花溅泪,春入愁城”,这样,愁就有了确切的去处。但仔细想来仍不如北宋朱淑真在《眼儿媚》中写出了意境:“何处唤春愁?绿杨影里,海棠枝畔,红杏梢头。”当然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北宋贺铸在《青玉案》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目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其立意新奇,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使我们终于知道了愁的去处。但仍无法结束该文,因为李清照曾说过“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作者简介】耿汉东,安徽省淮北市人,诗人,文学评论家,地方文化学者。先后供职于中共淮北市委宣部和淮北日报社。喜欢读书,敬畏文字,己创作出版17部作品,主编8部诗集。现为安徽省诗词协会副会长、淮北市诗词学会主席。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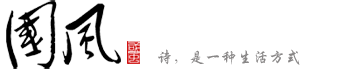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