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别人都对苍蝇嫌口吐味纸诛笔伐之际,我似乎没有碰到它伤害我令我讨嫌之事。我于是乎想苍蝇红脑壳,绿身子,透明如乳纱的翅膀,只是声音难听点,没有节奏感,这样的小东西长相还蛮好看,比在树叶上扭动的“千只脚万只脚”的毛毛虫美观多了。
在上个月前,我是不讨厌和反感它的。当然对它印象也不怎么深刻。上个月的某一天,来了个形势大逆转,这些“哼哼唧唧”“嗡嗡嗯嗯”的家伙让我愤怒到了极点,以至此时此刻,我仍旧想抓几只苍蝇过来给它们上一堂政治课,教育它们要恪守本份莫去做侵犯他人劳动成果之事。活了这么大岁数的我,除了刻骨铭心恨过叮在我身上手上脸上的蚊子外,其他任何动物我都不曾带恨意。
上个月的某天,太阳很大天气很热。上个月的某天还在春季里,不至于这样热的,可它就是热了。对它的热我也不可能拣块石头去砸天,事实上我这喊打“宝讲”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有哪个女子或男子从地上拣块石头砸到了天的脑壳,没有,从来没有,连天的脚指甲和头发丝都不曾碰到,何况我乎?
扯到这里,似乎不好接下文了,管他哩,我且自划自说着。
丈夫的亲哥哥说想去钓鱼,希望我能送他到我娘家叔叔的小水库里钓鱼去。我这个人很少做拂人面子的事,于是把他领到小水库,于是那天他发了财,钓了十几斤“鲫壳子”。这是自他从城里回来暂居在我们家开始钓鱼以来,首次钓这么多,钓这么欢,钓出匪夷所思钓出惶恐害怕钓出水里有鬼怪之类,钓出十几斤“鲫壳子”疑心是树叶变的石头变的。我听了他的惶恐和害怕后,我也开始装着浑身哆嗦,口齿不清,瞳孔扩大,俨然有鬼附身的样子。
他反而变得有味了,回家后,唱歌啼乐地拣了一脸盆大“鲫壳子”出来。这些“鲫壳子”匀匀称称地,都似一般大,我用手称称,五六两一条是有的,他把它们一一剖开。我在旁边看了一小会,就朝下屋的桂嫂家看打麻将去了。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丈夫的哥哥在桂嫂家的地坪上喊我“芳老案,芳老案,你出来回家把鱼放冰箱里哩!”“芳老案”这绰号是怎么来的?我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反正很多年龄大的邻舍都这样喊我。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很多人这样喊,大势所趋,我只好应答。丈夫的哥哥也这样喊,我也就大大冽冽应了。平时与他相处既像朋友又像兄妹,他喊,我就没有芥蒂地答。反正应答过后,我身上冇少坨肉。
他这样一喊,我真的往家赶,真的笔直朝灶房间跑。我刚跨进灶房间,你道怎么样?满房的苍蝇“嗡嗡嗯嗯”“哼哼唧唧”。我杀开一条“蝇路”,朝灶台上的脸盆奔去,整个一个惨啊!很多红脑壳绿身子薄翅膀的苍蝇趴在沒有用盖子盖着的鱼身上。看到人来,苍蝇们群飞而起,被丈夫的哥哥调好了各种香料的“鲫壳子”身上全是黄色的密密麻麻的苍蝇卵还是苍蝇屎。
我蹲在地上,边抱着头抵抗苍蝇的俯冲边用尽力喊“快来啊,老兄,鱼要不得了,这一脸盆鱼全要不得了……”
在外面忙別活的丈夫的哥哥三步并作两步奔进来。他也杀开一条“蝇路”到了鱼面前,傻了眼。
后来这盆鱼被我利用想象空间发挥到恐怖极至,我从吃了这有苍蝇蛋苍蝇屎的鱼联想到得瘧疾得瘟疫到抢救室,重症室,然后变成一条条“鲫壳子”溜直溜直……
丈夫的哥哥捂着耳朵皱着眉愠着脸连声叫“打住,打住,这盆鱼倒掉还不行吗?……”
大盆鱼虽然倒掉了,丈夫的哥哥又到屋后的小塘里重新钓了几条小鲫鱼,重新拌香料。
那天的晚饭,我就着丈夫的哥哥做的鲫鱼汤美美地吃了三碗饭,家里其他人也吃得酣畅淋漓。席间我想到倒掉的大盆鲫鱼,想到少吃的许多饭,怨意满齐了喉咙,恨不得将那逃掉的苍蝇一只只抓回来给它们上一堂政治课,抓回来上一堂让它们摸心问肚做事好好做蝇的政治课!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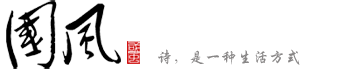
网友点评